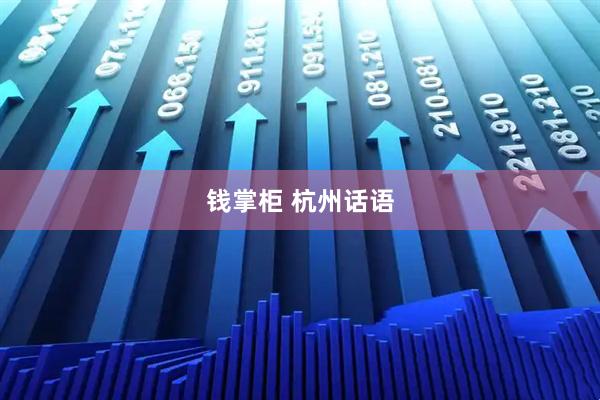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把上海话叫做“上海闲话”,杭州人把杭州话称为“杭州话语”。我生长在上海,会说上海闲话;因为曾客居杭州,也会些杭州话语。后家又搬回上海,成了会上海和杭州两地方言的“双语”者。
小时候,上海弄堂里有个顺口溜:“乡下人到上海,上海闲话讲勿来,咪唏咪唏炒咸菜。”这里的“乡下人”是指外省人,从市郊来的则叫“阿乡”;这点与巴黎人有点相像,出了巴黎都是乡下。住杭州时,却没听到过“杭州话语讲不来,咪唏咪唏炒咸菜”。
著名沪语播音员万仰祖告诉我:上海话要算徐家汇一带的本地人最道地钱掌柜,还说上海话里带点浦东音就会好听许多。杭州的研究者说:讲杭州话的是杭州城里人,城外乡下说的是余杭话,城里人称之“枪篱笆外头的话语”;这枪篱笆不是竹头的,而是砖砌的城墙。城墙位置就是今环城东、南、西、北路,我家所在的环城西路,大约就在城墙根下。
未搬杭州时,因爸爸所在部队驻杭,跟姆妈探亲来过几回;那时就知“儿”字是杭州话的特色和标志。刚搬杭州时,听邻居讲过“儿”的笑话。一北方人以为只要加“儿”就是会了杭州话,年纪大“老头儿”,年纪小“小伢儿”,鞋和帽叫“鞋儿”“帽儿”。于是,他进餐馆吃饺子如法炮制:“我要一碗饺儿。”没想遭服务员臭骂。杭州话“饺儿”可不是个好词儿。
那些名词后加“儿”的杭州话还基本能明白,动词后加“儿”的,理解就有点吃力。听到“搞搞儿”“耍子儿”不懂就问,原来就是“玩”,就是上海话“白相”。就说这“耍子儿”。当年南宋在杭建都后,随之而来的北方杂耍出现在杭州街头,去看杂耍叫“耍子儿”,后从看杂耍推至游玩等。记得在《西游记》读到八戒到花果山请悟空救师父,悟空说:“贤弟,累你远来,且和我耍子儿去。”说是作者吴承恩杭州生活留痕所致。
其实,带“儿”字的词汇也多在北方话里;它频频现身杭州话是宋时避战乱从北方逃江南不少,杭州城里外来人口超过本地土著,他们说话带“儿”影响了当地语言令杭州话南北掺杂,按电影导演岑范的说法还影响了当地人的相貌。有人说他执导的影片《阿Q正传》中,北京人王苏娅饰的吴妈就不像南方人。他解释道:吴妈先人是宋时逃难来的。我们听了大笑。
虽同属吴越之地,有些杭州话上海人听上去一头雾水。学农时,在水乐洞见几个上海人用溪水洗脸,我的同学劝道:“这水毛(意‘很’)风(意‘脏’)来”。上海人听不懂“风”就是脏,“脏”在上海话里是“龌龊”。此外,常用的“不”上海话发音“勿”,杭州话是“表”,发音相差好几条横马路。“迁”就是上海人的“嗲”,“毛迁来”就是“老嗲呃”。还有绳子叫“索儿”“介个套”是“怎么样”等,这些杭州话是打死上海人也猜不到是什么意思。
杭州话也有同上海话接近的,如乒乓杭州话读“BING PONG”,上海话读“PING PANG”。也有不少杭州话同上海话如出一辙,有一个字的潽、烊、囥等,两个字的辰光、头颈、落胃等,三个字的墨墨黑、雪雪白、寻开心等,四个字的一榻括子、神知无知、吓人倒怪等。
读大学时,著名独角戏演员姚慕双先生来做讲座。说他友情提醒驻华外交官:在中国要学会三种话才能走遍天下,除普通话,还有两种是方言——广东话和上海话,没有杭州话。作为一地的方言,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与它生存的土壤有关。
杭州话也有它的骄傲和自豪钱掌柜,就是能听到125年前的杭州话语。这段杭州话的录音,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,由法国语言学家莱昂·阿祖莱1900年用蜡筒录音。这真叫上海闲话好生羡慕啊。
天弘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